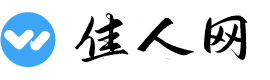雪花中的艺伎,就像飞舞着的精灵
“纸灯下施着粉黛的笑。
“竹窗里晨起的慵懒。
“闲散时浮生里的短暂欢快。
“是繁华极艳,却又隐藏着悲伤之哀。”
日本的艺伎完全是肉身艺术品的究极姿态。这种艺术品既有高度的美,又具有满足大众游玩的要素。艺伎象征日本人美意识。艺伎的一举一动都在美的规范下样式化。艺伎个人的情性(如果有的话)只能隐藏在职业的假面背后。艺伎通常继承先辈的名字,脸上涂上很厚的白粉,所以你是谁,她是谁,你与她有何不同,基本没有。她们是一个化验室里出来的“无臭”标本,或者说是同一试管里出生的“婴孩”,又或者说是一棵树上开出的山樱花。
作家永井荷风在其《江户艺术论》中曾这样描写日本的艺伎:凭倚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她们总是令我欢喜。
谷崎润一郎为日本艺伎设计的意象是:京都美人、往昔祗园艺伎们的花容月貌、清幽小庵、绉绸、雪白肌肤、香绫泪、脂粉、裙边、紫色、灰紫色、茶室、孤寂、茶釜之音、炭香、熏香、一株山茶花。
这是一个神秘的青春女子世界,这是一个充满迷幻的为上流社会男性客服务的“圣地”。因为神秘,因为迷幻,所以300多年来,日本的舞伎、艺伎又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巨大的“黑洞”。因为是黑洞,所以又吸引了为数不少的日本文人学者来解构其谜。
京都特有的凛冽寒冬,并不好过。纷纷飘落的飞雪,冬日夜晚的寒气,愈发沁人骨髓。雪粒敲打着葛藤铺茸的芦庵屋顶,噼啪作响。
一位头戴十二月花簪的美丽艺伎,身着浅色素雅的和服,足蹬高高的木屐,右手轻巧地撑著白色丝绸的伞,静静地伫立在茶屋的门前。暮色时分,团团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在舞伎的周身飞舞。
静谧。寒风。冷雪。
雪花中的艺伎,就像飞舞着的精灵。
艺伎的边缘诗学——粹
毫无疑问,艺伎作为一种文化,如果没有一种理论上的或者说是哲学上的关照,它的色彩就会黯淡很多,它的腔调也会弱很多。在人们的观念中它的认知性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从哲学上完成对艺伎知性的关照是九鬼周造(1888—1941)。这位“东洋的贵公子”(大桥良介语),发明了“粹”这个日本式的独特的概念。他在1930年42岁时出版的《“粹”的构造》一书,是在巴黎写成的。他在巴黎哲学名人堆里,用“粹”这个无法翻译的概念,玩转于东洋与西洋之间。因为西方人怎么也不会知道,粹是与江户时代欢场同时成长的一个概念。
九鬼的父亲九鬼隆一是驻美全权公使、贵族院议员。母亲波津子是京都花柳界出身的美貌艺伎。而母亲在回国的船上,又与陪同她回国、写有名著《茶之书》的冈仓天心擦出恋的火花。火花一燃就是九年。冈仓天心为此失去了美术学校的校长职务。母亲的不伦给九鬼带来思考:理想化的女性究竟为何物?
九鬼带妻子缝子去欧洲留学是在1921年。33岁的时候,九鬼因遍历欧洲美女,缝子与他离婚。九鬼甚至写出了这样的诗句:“路易丝为了取悦我/身着日本刺绣的衣裳而出。”他的第二任妻子中西菊江是一位年轻的艺伎。同时九鬼还暗恋着好友岩下壮一的妹妹,据说也是一位艺伎,因此他对艺伎的感觉更为感性直观。通过考察艺伎的本质,思考艺伎的文脉,他发现用“粹”(いき)这个日本语来表述艺伎是最为妥帖的,他说:“所谓粹就是东方文化的,或者说是大和民族特殊存在样态的显著的自我表明之一。”其极致就是“民族存在的解释学”。而粹的结构被解析为“对异性的媚态”、“意气”和“达观”。
这个“粹”字的巧妙在于:它否定了用色情一词来涵盖或轻视艺伎的倾向。但是它抓住情色世界里男女双方极尽能事的风流或装模作样,被强迫观看的外貌,更是在表面上是出卖色相的艺伎,简约为淋漓尽致的快意的人生态度。艺伎在男女交往中看似属于被“侵犯”的主体,如狎妓商人或男子与复数的艺伎打交道等。这时的艺伎要如何保持不被迷惑,不被“侵犯”,这就需要通晓色道,通晓人情奥秘等的对人性的极致认知。九鬼说这就是“粹”,一种和式的审美意趣。九鬼曾经向海德格尔阐述过何谓粹?这个时候他的语言也充满了粹:“所谓‘粹’就是像和风吹过来,明亮闪耀,为之吸引的静谧。”
九鬼从原理构成的角度,将粹限定为三个主要特征或者说内涵:
第一是对异性的“媚态”。
第二是来自武士道的“意气”。
第三是来自于佛教的“达观”。
何谓媚态?晚唐诗人崔钰写过“朱唇啜破绿云时,明目渐开转秋水”美人饮茶的诗句,这是否属于媚态?但九鬼的视角是全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