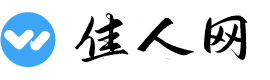本期话题
司马相如是两汉文学史上最巨大的作家,可是关于他的创作阅历却始终云山雾罩,扑朔迷离。
部分历史学者以为,司马相如是在赀选为郎、游宦京师之后才开端了他的文学创作,可是这样一算来,距离他写出不朽的《子虚赋》就只有几年的时光。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年青人,真的能在几年的学习之后,成为西汉赋圣吗?
与卓文君成婚,无论婚后的生涯和情感毕竟怎么样,司马相如最初酝酿这件事的时候,应当是有筹划要借卓氏的财力赞助自己重入赀选,再度出仕的。可是命运的轨迹却没有依照他的假想展开。
在蜀郡蛰伏了6年之后,司马相如终于重新得到了皇帝的征召。但这一回不是通过赀选,而是皇帝读到了司马相如几年前在梁国写的一篇《子虚赋》,对他大为赞美——顺便说一句,这时的长安已经改天换日。那个不好辞赋的孝景帝逝世了,新继位的孝武帝刘彻出人意料地成了司马相如的“知音人”。
读过相如的旧作,司马迁说,孝武帝的反响是这样的: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南朝学者刘勰曾经说过,赋这种文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它原来就是一种深入烙印着楚地文化的文学样式。而自西汉开国以来,君臣贵胄又以楚人为多,所以辞赋便借着乡音的感召,顺理成章地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贵族们雅赏清吟的篇什。
具体到孝武帝刘彻,他自己就是一个作赋的内行内行。爱妃李夫人逝世之后,武帝为追悼她而作的《李夫人赋》,直到今天仍是赋史上不朽的名篇。
可奇异的是:鉴赏《子虚赋》的时候,孝武帝居然打了眼:“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很显著,武帝把《子虚赋》算在了另一位他熟习的作者头上,而这位作者在武帝说话的当时已经遗憾作古。直到旁人告知武帝此文乃蜀郡司马相如所作,孝武帝仍然大吃一惊,表现不可思议。并在随后召问了相如,以作确认。
为什么孝武帝会发生这样的误解,他毕竟把《子虚赋》算在了谁的头上,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和这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答复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相如学赋的阅历语焉不详,我们甚至无法探知他从什么时候开端接触到了辞赋。我个人的断定是,至迟在司马相如以赀选入侍景帝为武骑常侍的时候,他已经熟练地控制了辞赋的创作技能。因为《司马相如列传》说: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太史公说“会(也就是碰巧)景帝不好辞赋”,言下之意似乎是司马相如擅长作赋的专长在汉宫之内得不到应有的观赏。孝景帝不过把他当做一个寻常的骑郎来对待。这对于一心追慕古人出将入相的司马相如来说,难免生出怀才不遇之慨。而碰巧梁国愿意礼遇辞赋作家,梁孝王此时又正无穷接近一人之下的嗣君之位,司马相如由此便动了东游梁国的心思。
如果司马相如这时候还不会创作辞赋,他不大可能被梁国的同好如邹阳、枚乘等辈所吸引;如果此时他的辞赋创作还达不到相当的程度,他也不可能盲目自负,自负他能够从梁国众多的文学侍从之中脱颖而出,赢得梁孝王的赏识。可是司马相如究竟来自偏僻落伍的蜀郡。
在他横空降生之前,蜀地还没有涌现过第一流的辞赋作家,那里也不是辞赋创作的重镇。换句话说,司马相如不可能闭门造车,在故乡练就写作辞赋的本事。要照这样推论下去,这位西汉赋圣就只有一个机遇开启自己的辞赋创作生活了。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三国志·秦宓传》
秦宓的这段话,在今天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质疑他所说的相如东受七经是对《汉书》的误读。质疑者的其中一条主要理由是,依据《汉书·循吏传》的记录,庐江人文翁出任蜀郡太守的时光是在景帝末年——大致相当于景帝后元年间,即公元前143年至公元前141年——而此时,司马相如已经停止了在梁国的游宦,返回蜀郡与文君成婚了,他怎么可能接收文翁的派遣,东受七经呢?
秦宓既然在他写给王商的书信中提到了《汉书·地理志》,那也就是表明他清晰《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录。可他为什么没有理会《循吏传》的那一句“景帝末”,仍保持说出了相如东受七经的话?
秦宓留下的这个疑问,后来的东晋学者常璩做出了新的说明,他在《华阳国志》一书中将文翁任蜀郡太守的时光从景帝末年改定到了文帝末年。当然,也就因为这一违反《汉书》的改定,常璩和秦宓一道被部分学者打入了不可信从的野狐禅之类。
但是,否认秦宓和常璩的人似乎疏忽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两位学者距离司马相如的时期并不遥远,而且又都擅长蜀地。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疏忽《史记》、《汉书》的相干记录,保持认定相如曾经东受七经呢?
我私意认为,这不能一边倒地责备是他们两位在杜撰,而是《史记》和《汉书》关于司马相如的记录本身就存在显著的缺失。
司马相如是以一个辞赋作家的身份被列为传主的,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这位作家早年接触、学习以至创作辞赋的阅历却没有哪怕一个字的记录。直到建元三年孝武帝读到了那篇《子虚赋》,一代赋圣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那样横空降生了。这样的故事让人如何能够信任?
当然,造成这种局势恐怕也不是太史公所乐见的,多半还是修史的资料缺失所致。西汉时候的蜀地僻远闭塞,与中原的文化交换相对较少。
司马相如成名之前,中原人士中有谁会去关注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年青人有过怎样的学习阅历呢?为史料所限,《史记》对传主的早年阅历记录不明的情形时有产生。别说司马相如了,就连赫赫著名的开国功臣韩信,司马迁都没能在《淮阴侯列传》中把他早年的军旅生活交代明确。公元前206年,籍籍无名的韩信突然被刘邦拜为大将。
可是在司马迁的记录中,韩信此前连一场象样的战斗都没加入过,此后却克服攻取,无往不利。这样的“神话故事”就跟公元前138年司马相如因《子虚赋》一夜成名一样,都像是脱了页的线装书,前因效果完整断了篇儿了。
让我们再把话题说回到司马相如身上。为《史记》作注的唐代学者司马贞以为,秦宓说的那段相如东受七经的业绩正好可以弥补《司马相如列传》的记录缺失。具体地说,就是下面这一段: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在这段记录中,“少时好读书”和“相如既学”指向的该是两段不同的学习阅历,不可以将“既学”误认作是“少好读书”。因为汉代学术极其看重师法。严厉意义上的求学,必需要投拜名师,树立起学术上的师承关系。这跟自学成才基本不同。如果司马相如不曾拜师,也就谈不上“既学”(即毕业)。
再者,司马相如少年时期爱好读书和击剑,亲长为他起名“犬子”。这很可能是称赞他击剑时身手敏捷——所谓“犬”,其实就是“剑”的谐音字。这意味着少年司马相如的兴致所注乃在舞刀弄剑而非舞文弄墨。可是“既学”之后,他连志向都转变了。这位从前醉心于剑术的少年转而崇敬起鼓唇摇舌的战国名士蔺相如来。从武行一下子跳到了文行,这显然不是“少时好读书”而是后来“既学”的影响所致。
司马相如早年要是有过一段求学的阅历,他上哪里去求学,又拜谁为师呢?司马迁说不明确。班固也做不出有益的弥补,但是《汉书·循吏传》中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喜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造诣还归,文翁认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汉书·循吏传》
蜀郡太守文翁曾经遴选了十多位本乡子弟到长安求学。这些公派学生有的进入博士官学习儒家经典,有的分派到别处学习朝廷律令。几年之后,学成回蜀,这些人就成了中原文化在蜀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种子。
秦宓和常璩都认定司马相如是这十多位公派学生中的一员。他们的看法精确与否先不说,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那就是司马相如要想接触到辞赋创作,就必需走出蜀地,走进风行辞赋创作的某个地区文化圈子,而汉都长安正是那样的一个处所。
说到这里,质疑者或许会提出疑问:既然学习辞赋是司马相如来到长安之后的事儿,那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明白记录,相如以赀选为郎,到孝景帝身边做武骑常侍,他学习辞赋创作会不会是从那以后才开端的呢?我个人私意认为,这种假设的疑点太多,很难成立。
其一,司马相如既然志在仕途,而孝景帝又不好辞赋。那相如此时学赋岂不是毕其功于无用之地?
其二,公元前150年梁孝王入朝之后,相如随他去了梁国。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所载,梁王在京的那段时光“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皇帝和梁王的娱乐重要是游猎,不见举办文人雅集之事。景帝既然对辞赋没什么兴致,也不太可能与梁王一起举办这样的雅集。
如果司马相如不是早就倾心于辞赋创作,对这个范畴内的顶尖作者素有所闻,他怎么可能被吸引到梁国去?难道他以天子近臣的身份私下结交诸侯侍从?那可是犯了大忌讳了。
其三,去往梁国之后,梁孝王以诸生之礼安顿了司马相如。这其实侧面印证了司马相如曾经入博士官做过弟子,否则梁王怎会以诸生视之?
其四,就在梁国的那段时光,司马相如创作了《子虚赋》,而这是一篇代表着西汉辞赋创作一流程度的文章。假设司马相如学赋乃在赀选为郎以后,距离他创作《子虚赋》也就只有几年的时光。一个来自边沿地带,半路出家的年青人才学了几年辞赋,就一跃成为这个时期的顶尖作者。这就好比一个中国少年去巴西学了几年球,你能理想他的程度超出罗讷尔多吗?
有鉴于上述这些疑点,完整否认秦宓和常璩关于相如东受七经的记述恐怕是有欠郑重的。至于他们和班固在文翁兴教的时光上涌现争议,我更偏向于以为秦宓和常璩的记录并不是以《汉书》为据,可能别有传播在蜀地的异闻作为底本。至于两派说法谁更可信?虽然《汉书》的记录的确要早于秦宓和常璩,但它也只是孤证而已。
如果我们信任司马相如曾经东受七经,并在此进程中开端了他的辞赋创作生活,那就意味着相如的辞赋应当接近于西汉京城长安的风行作风。
可要是这样的话,生于长安、擅长长安的孝武帝对京城文化圈如此熟习,又怎么会把《子虚赋》的著作权算在别人头上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我们还得到司马相如游宦的梁国去持续追寻。
参考文献: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
王先谦《汉书补注》[M];
何一民、崔峰《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J];
刘南平《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考》[J];
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J];
王增文《论散体大赋生成于汉景帝时代的梁国》[J]。
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掩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接洽授权。
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勉励 !
— THE END —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