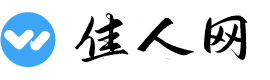转自:经典与解释
“dialectic”,即现在所说的“辩证法”。它是中国知识界开眼看世界后从外国引入本土的一个概念。从历史看,这一译名无疑是成功的。它已经融入国人平时的思维活动和言说习惯中,成为最常用的概念之一。然而,在它被译介入本国时,并不是一片叫好声,其中亦不乏杂音:贺麟主张译为“矛盾法”,张东荪则前期主张译为“辨演法”,后来译为“对演法”。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杂音被过滤,消弥于急迫的现实中。随着境况的转移,时势的不同,重新聆听这些音符,并进行认真的打量,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一、 对“辩证法”译名的异议
“辩证”和很多现行通用的词一样,是直接从日语中转译过来的。从日本转译,无疑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著作的一个方便途径。当时的中国因闭关锁国而自我封闭,与西方国家差距甚大。要跟上西方发展的步伐,重振中国,必须了解西方,因而译介的任务极其迫切。而日本对西方的开放比中国先行一步,由于其地缘因素,以及文化上的同质,便于进行迻译。这种迻译,势必引进大量的日本名词。王国维曾分析遵从日本译名的优点:“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此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1
王国维对倡导用日译名词的作用有多大,可能一时还难以估计。但是,“辩证”译名是否贴切,却是有争议的。在日语中,“辩证”一词其意义为“弁别し考证すること”,2意即为辩别与考证,与中文的字面意思一致。对于这种译法,至少在瞿秋白那里,就遭到了质疑。瞿留学苏联,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功臣。他在1924年就将“dialectic”译为互辩法,3明显不满于日译。其理据可以从同时代人的评述中得出:“辩证法这个名词是从‘第亚力克谛’(dialectic)这个外国文译过来的。‘第亚力克谛’是古希腊文,原是‘辩论术’,即互相辩论可用何术屈服对方之意(所以瞿秋白主张译为互辩法)。”4而更早对“辩证”译名提出异议的可能是张东荪。张在“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 5,连其反对者都赞成。他在《新哲学论丛》中提到:“黑格尔的辨演法(dialectics旧译辩证法很不切)就是以为甲必有待于非甲;于是由正而反,由反而合,乃演化出来。” 6和瞿秋白不同,瞿后来并没有重提译名一事,而张将译名稍稍改造,在三十年代继续重提译名问题,其所据的理由一样,下文再及。
然而,这次译名的异议并没有引起注意,或者是由于当时知识界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唯物史观以及两大西方哲人的访华。1927年后,“唯物辩证法风糜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任何顽固的旧学者,只要不是甘心没落,都不能不拭目一观马克思主义的典籍……” 7。这段评价虽有夸大的嫌疑,但辩证法成为时髦却是事实。但是,在辩证法的极盛时代,对“辩证”译名的讨论几乎没有,这显然与中国的致用思维有关。
到了三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深入研究其中学理提上了日程;同时,在传播过程中,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者内部出现了分歧。正确深入了解辩证法,刻不容缓。然而就文本而言,马恩关于辩证法的说明不多,但马恩曾自述是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黑格尔哲学在马恩的捆绑下,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冷清,终于出现了小小的热潮。如果说马克思当年曾得益于黑格尔不少,那么马克思已经十倍奉还于黑格尔。新视野的出现,消解了原有的惯性,给译界注入了新的生机,讨论“辩证”译名的文本多起来。首先是留欧的贺麟。他在30年将其译为“矛盾思辨法”8,在稍后的《〈黑格尔学述〉译序》中,明确提出反对“辩证法”的译法,主张用“矛盾”译“dialektik”。9另一提出异议的是张东荪,他一直批评“辩证”译法,主张译为“对演法”。10两人的讨论是从黑格尔哲学入手的,共有着同一个平台,而且有着不同的翻译根据。
二、各自的学理
贺麟和张东荪对“辩证”译名的批评,虽然共有着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一个讨论平台,但其切入点非常不同。
贺麟在《〈黑格尔学述〉译序》中说:
“……就是黑格尔的Dialektik 或Dialektische Methode既是指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及意识生活之矛盾分析等,则其含义与普通所谓‘辩证’实显然隔得很远。若依日本人之译西文之 Dialektik为‘辩证法’实在文不对题,令人莫明其妙。即译普通逻辑哲学家用以驳倒对方之dialectics——即译近于诡辩而实非诡辩的矛盾辩难法为‘辩证法’,虽勉强讲得通,但亦欠确当;因为‘证’字含有积极地用实验以证明一个假设,或用几何推论以证明一个命题之意,而矛盾辩难法的妙用只是消极地寻疵抵隙,指出对方的破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不一定要证明一个命题或假设。所以我将Dialektik一字统译为‘矛盾法’,而可以通贯适合于各种不同的用法:如矛盾的实在观,矛盾的真理观,矛盾的辩难法,矛盾的分析,矛盾的进展或历程,先天的矛盾(或先验的矛盾,如理性偏要发宇宙起源的疑问,但又不能回答),矛盾的境况(凡两难的境况就算是矛盾境况,如狼之与狈,如既不乐生又复畏死的境况等)等等。……而且我们试一下探黑格尔的生活与性格,则知他自幼即喜欢注意矛盾的现象。如他在日记中常记载些‘年青之时,想吃不得吃;年老之时,有吃不想吃’。和‘晚间应各自回去睡觉,白天再来观看星宿’等矛盾趣谈,便是好例。所以他后来在哲学上所用的方法便叫做矛盾法,实极自然的趋势。”11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贺的理由:从“证”字着眼,破“辩证”的译法行不通,“证”是积极的,而“dialectic”是消极的;从译文的一贯性来强调“矛盾”译法的优势,希望在各家各种不同用法中取得全面合理的平衡;从黑格尔的生活与性格来论证“矛盾”译名的可行性,则又过分强调个体性,与其一贯性的主张存在着潜在的紧张。贺所拈出的“矛盾”一词是本土词汇,由韩非的寓言衍生而来。实际上,从词义来看,本土的矛盾与“dialectic”相去甚远:矛盾只有一矛一盾两个方面;而黑格尔的dialectic其重要创见则在于矛和盾外的第三个维度。要解构固有的看法而重建新的意义,一般而言其成功率与词语的使用、熟悉程度成反比,这反倒不如建构陌生的“辩证”一词来得容易。另外,“矛盾”一词将同时对应两个不同的外来词:dialectic和contradiction,这两个词在哲学上似乎有着不同的意思,且意思有相对之处,译为中文时如何区分?可见,“矛盾”译法并不见得比“辩证”译法更高明。当时就有人指出“中文矛盾两字,只有两相敌对的意思,绳之以黑格尔之dialectic,似最多能与‘正’‘反’相比附,而毫无‘合’的含意。‘合’在黑格尔之dialectic中最重要,绝不该抛弃。并且译为矛盾法还很容易和另外逻辑上的‘矛盾律’相混淆。”12贺的译法,似乎没有其想象中的好。但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
与贺强调一贯性相反,张东荪更看重个体性和差异性。他不辞劳苦地从dialectic的演变着手,通过分析此概念在各个哲学家的具体意义,点出其通译的困难,得出“并且就各家所主张的内容而言,这个字译为‘辩证法’便有许多地方不得其宜。严幼陵先生主张一字数译,即完全看他的意义而变。现在的人们实在太忽视这一点了。我亦主张译外国名词随其涵义而不同。”13因而他按着黑格尔的用法,将其译为“对演”。无论是他五四时译的“辨演”还是以后的“对演”,都对“演”字进行强调,这显然基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认为黑格尔的dialectic是一个历程、一种“动的逻辑”。这一译法集中于黑格尔的个性,而过滤掉了其他人的用法,诸如柏拉图偏重于辩的用法。就黑格尔的用法而言,确乎比上面几种译法都好,更贴切。“因为‘对’足以概括opposites即‘正’与‘反’。‘演’足以概括‘变动’(becoming);既有‘变动’,于是有综合(synthesis)。比如拿‘有’(being)来说吧,先有个‘有’,同时又得到‘无’(nothing),由‘有’到‘无’,由‘无’到‘有’,于是立刻又演绎出‘变动’。即‘有’、‘无’、‘正’、‘反’的综合。”14
概念的演变其实也是文化的积淀。同一概念符号,随着历史的变迁,负载着历史赋予的不同意义。对于异质的文化来说,如何将这种层积的历史意义尽可能地对译出来,这是翻译必然面对的难题。张在这里,提出了这一问题,主张译法具体到每一个人。这样,必然使得在原来文化中本来是同一的词,翻译后变成不同的词,造成阅读时出现理解的不连贯,将原本有着关联的词从文化中硬剥出来之感。
贺、张依据的都是黑格尔哲学,都从黑格尔dialectic的内容出发,明显异于瞿“互辩”对“dialectic”形式的看重,并且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据。但是,一个主张译名的一贯性,一个主张译名的具体性;一个从共时性出发,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以通用于所有的用法,一个从历时态出发,要求具体的切合。
不管优劣如何,两种努力在当时都有相同的命运:没有得到重视。贺在后来不再坚持“矛盾”译名,显出其机智;而张几次提到译名问题,被认为罗嗦。下面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态:“本来咬文嚼字是非常空虚无聊的事,张东荪教授反对将Dialectic译作辩证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应用名词,要紧的是内容的把握,而不是一个名词的形式。形而上学者张东荪不问内容而单看重形式,是他的方法论使然,这倒不能深责他这个人。”15当然,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多因素的:一是中国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过多地讨论这些似乎不关紧要的译名问题,二是传统的实用理性作怪,三是张对译名的紧咬不舍,似乎不纯是出于讨论学术问题的动机。
三、背后的原因
要人相信或接受某个概念、价值或理论等,需要以普遍性张目,这样才能推广出去,让人信服,这就要求必须具有学理的支撑;然而,每个有意识的行为,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促使行为者作出不同的选择。就翻译而论,按照现代西方解释学的说法,翻译过程是翻译者和被翻译文本间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因而,翻译者的行为动机、文化传统,通过被翻译文本,集中地体现于翻译出来的文本中。探究背后的原因,或许更能理解译者当时的“所想”。
就贺而言,“矛盾”译法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黑格尔学述〉译序》中,直接提出从事翻译的三条原则:
“(一)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
“(二)作文应打破文言白话的界限,而以理明辞达情抒意宣为归;
“(三)翻译应打破直译、意译的界限,而以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为归。”16
因为要履行这三条原则,所以书中有“不少的不中不西亦新亦旧的材料和名词”。这是对诸如“矛盾”这种打破中西新旧译法的正面阐述。对西方学者生硬造词译太极这一中国概念时,则是对翻译原则的反面论述:“他们(指西方学者——引者注)只知道生硬地去新造些名词来译太极,而忘记了在西洋形而上学上去找现成的且含义相同的名词以译之,所以未采取Absolute一字。”17从一正一反的实例中,可以看出贺非常强调从本土哲学中寻找相应的译名对译外来的哲学,这并不是偶然的。紧接在一正一反的意见后,终于亮出了底牌:
“此外我还有一点微意,就是我认为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译名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所谓有文字学基础,就是一方面须寻得在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第二要有哲学史的基础,就是须细察某一名词在哲学史上历来哲学家对于该名词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作法;同时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以译西名,但须极谨慎,且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这倒并不是在学术上来讲狭义的爱国反日,实因日本翻译家大都缺乏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字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工夫,其译名往往生硬笨拙,搬到中文里来,遂使中国旧哲学与西洋的哲学中无连续贯通性,令人感到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好象完全是两回事,无可融汇之点一样。”18
贺和王国维对日本译名的评价正相反,颇可玩味。贺的批评点在于日本译名由于缺乏本国文字学基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有将中西哲学分割成两段的弊病,使得中西哲学失去其互通的可能性,即失去了“中国化”的可能性,因而强调要慎取。
这种慎取反映了贺想将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企图。哲学概念是哲学的灵魂。在传统中寻找适当的译名,无非是寻找适当的契合点,以便合理有效地连结两者,融会贯通中西哲学。其根据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其直接外在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积弱。因而,“翻译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华化西学,使西方文化中国化。中国要想走向世界,首先就要让世界进入中国。为中华文化灌输新的精华,使外来学术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移译、融化西学,这乃是中华民族扩充自我,发展个性的努力。”19贺后来走的学术救国之路,所创造出来的新心学体系无疑都是践行此策略的最好明证。而当新中国成立后,贺对译名的看法发生了转变20,从强调译名的本土化转为精确性。这更显出前期的用意和时代的要求的紧密相连,因为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变了。
贺后来不再提起“矛盾”译法,毕竟知大潮不可逆,况且当时的要务不在此。而张东荪则是另一种姿态。在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论战中,紧揪住“辩证”译名不放。他所著的书,对“辩证”译名从来就没有停止批评。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两文更不厌其烦地大谈辩证法的历史。然而,这并不能赚来半点的赞赏,反倒被认为是“对于问题的讨论,也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于是“罗嗦”别有企图等。张可能真是另有所图。但是,说他“一方面他是企图从这不关紧要的方面,来避开对唯物辩证法正面的摸触,因而想抹煞唯物辩证法的真理性。一方面是把马克斯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一切唯心论的辩证法混合起来”21,这似乎误读了张:在这两篇文章中张并没有正面避开辩证法,只不过他曲解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意义;同时,他不是要混淆历史上所有的辩证法,相反,他把每个哲学家使用的辩证法含义试图进行区分,从而主张为各人订做不同的译法,“照其字的异义而异译”。
或许,从两次不同的译名中,我们可以发现些许端倪。张所强调的是“演”字,显然与他的理解有关。张佛泉曾经解释道:“黑格尔之dialectic method ,以有becoming为最要。黑格尔将becoming引入逻辑,是逻辑史上最大的改革,所以在译dialectic时,becoming的意思绝不能忘掉。我说张东荪先生译为对演法比较着妥洽得多,也就是这个原故。”22张佛泉的理解无疑切合张东荪的想法。因为在张东荪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证历程,而不是辩证方法。“所以黑格尔的‘辩证历程’是表现‘理性的自身发展’。就是说理性如何自己在那里动。而这个理性就是形而上学的‘本体’。理性既在本体论上则非论理学上所谓的‘思想’了。所以学者无不公认黑格尔的名学就是形而上学。换言之,他的名学绝对不可当作方法学来看。因为普通论理学大部分就是方法学。他的名学既不是方法学,则他的辩证法便不是思想上的方法。”23而马克思不是“一个哲学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便是把思想上的辩证法变为事实上的辩证历程”24,歪曲了黑格尔,因而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社会是行不通的。三番几次讨论“对演法”的译名,张寄望于突显黑格尔辩证法的历程性质,使人注意两者的所谓差别,以便实现他攻击马克思的企图。在其《〈唯物辩证法论战〉弃言》中,他声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因为本书著者数人可以说差不多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倘共产主义一辞与社会主义有一部分相同,亦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反对共产主义。”25他所指的“赤色哲学”无疑就是马克思哲学。可是,这一策略无疑是失败之作。当时众人关心的是如何自强,主要是实践问题,注重的是好不好用,根本没人关心译名的事,反倒授人以柄。
四、余论
从上可见,辩证法的译名是与中国传统的致用思维紧密相连的。而求致用,则不可避免地卷入对现实的估计。当时的现实不容许花太多的时间对译名进行订正,关键的是内容,而不是细枝末节,毕竟在那个时代更需要注重用的效果。因而,在初传时几乎没人质疑“辩证”译名的适合与否。而当贺、张好不容易寻找到黑格尔作为讨论的平台,带着自身的目的切入这一问题时,却缺乏必要的响应。
然而,辩证的译法和很多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名词一样,与传统的连续一贯相比,确乎显得有点生硬而突兀。事实上,中国很早以前就有辩证连用,但其意义与字面意义一样。似乎当时的国人并没有留意26。另外,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编著的英华辞典《英华韵府历阶》,英语名为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1844年在澳门出版,其中用辩证对译DISPROVE。汉语的字面意思与现代相差无几。27因而,就字面而言,辩证的译法不是最好的,至少不比张的“对演”好。显然,张的译法更符合中国的传统用法。但是,由于张的立场,这是不可能为当时人所接受的。国人惯于将言行一致作为评价的准绳,而不是进行恰当的分离。这种知行合一,又由于传统的致用传统,便常常与政治挂在一起,故而中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
当然,“物谓之而然”。但是,好的译名能使人透过符号猜知其意义,只需读者具有相应的传统文化知识。而不好的译名,由于符号与意义的脱节,无法从字面猜测内容,只能在传统外进行重构。更有甚者,会导致误解的出现。因而,译名似乎就不仅仅是咬文嚼字的小事。
但是,和很多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名词一样,辩证法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传统中的一部分,参与并塑造着未来的中国文化,现在再对其更改确乎没有必要。但是,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翻译将越来越多,面对译名,至少应该谨慎,免去社会的干扰,进行独立的讨论。
或许,其意义就在此。
1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1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
2 《新版日汉词典》,中国商务印书馆·日本小学馆发行,1991年北京。
3 在《社会科学概论》中,瞿写道:“唯心论的最高点已经探悉人类的观念之流变的公律(互辩律,旧译辩证法,Dialedtique——‘正反相成,矛盾互变。’)”(第939页)书中将“辩证的”称为“互辩的”。参见《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在1924年发表的《李宁与社会主义》亦提到“相反相成的互辩律”,载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国中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一册)。
4 戈人:《大众新哲学》,第100页,天下书店1939年。平生的《新哲学读本》(珠林书店1939年十一月初版)第122,123页有同样的一段话。只是后者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何人,而笼统地说“有人主张译为互辩法”。从两段引自不同作者同年出版的不同著作的相同解释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说明。
5 郭湛波:《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第14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6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19年8月初版,1934年3月国难后第一版。
7 艾思奇:《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载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国中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一册)。
8 贺麟在《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中说:“黑格尔全系统的中坚是矛盾思辨法(dialectical method)。”载于《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9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10 张东荪在《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等文章中都集中论述到。在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西洋哲学史ABC》中,讲到黑格尔时,认为“他这种法则即是所谓‘对演法’(dialectic旧译辩证法系袭取日本人,实在完全不通)。”
11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学述〉译序》,第652,6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12 张佛泉:《黑格尔之对演法与马克思之对演法》,载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九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13 张东荪:《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里有着同样的说明。均见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二册)》。
14 同注12。
15 艾思奇:《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载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二册)》。
16 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学述〉译序》,第64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17 同上,第658页。
18 同上,第662页。
19 贺麟《译名论集·序》,张岂之、周祖达主编《译名论集》
20 在《译名论集·序》里,贺对译名表现得更为宽容,不再强调译名的中国化问题,而转向准确性。这一转变在王思隽、李肃东著的《贺麟评传》的注释里提及,是颇有见地的。
21 秀侠:《张东荪的哲学——对提出的“辩证法各种问题”的驳复》,载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三册)》。
22 张佛泉:《黑格尔之对演法与马克思之对演法》,载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九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23 张东荪:《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载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三册)》。
24 同上。
25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弃言》,载于钟离蒙、杨凤麟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三册)》。
26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五·诗文托名》:“自赵松雪误为西山之作,世遂成论也。〔宋太史景濂〕辩证甚悉。”在此处,已经有连用,但其意义为辨析考证,用言字作形旁,表明是用言语。
27 转引自陈力卫:《从英华辞典看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原学》第三辑,陈少峰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